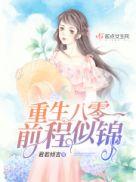第7文学>穿越成细作被嬴政偏执爱 > 6070(第7页)
6070(第7页)
赵偃沉默片刻,忽然道:“那你可知,李牧近日屡次上书,说你通敌叛国?”
郭开瞳孔骤缩,随即伏地大哭:“李牧将军这是要逼死臣啊!他手握重兵,臣不过一介文官…”话到此处,他猛地想起嬴政交代给他的事,当即抬头,独眼中迸出恨意,“大王明鉴!李牧屡拒王命,究竟是谁有不臣之心?!”
赵偃盯着他看了许久,终于缓缓靠回王座,摆了摆手:“罢了,你且下去养伤。”
郭开重重叩首,涕泪横流:“谢大王!谢大王!”
郭开退出大殿,脸上的悲戚之色瞬间褪。去,他拖着瘸腿转过宫墙拐角,独眼中闪过一丝狰狞的冷光。
赵偃,你倒是长本事了。
他攥紧袖中的手,方才在大殿上,他分明察觉到赵偃眼中的猜忌,这个昏聩无能的废物,竟敢在他为国负伤之际暗中筹谋另立丞相,以为他远在秦国就不知?
赵国朝堂,可都是他郭开的人!
他冷笑一声,胸腔里翻涌着毒火般的恨意,嬴政说得对,赵国早已腐朽透顶,赵偃这等庸主,根本不值得他效忠!
寒风呼啸,卷起他染血的衣袍,郭开眯起独眼,望向远处巍峨的宫墙,心中已是一片杀意。
既然你不仁,就别怪我不义。
他伸手入怀,指尖触碰到那封密信,那是临行前嬴政亲手交给他的,只要按计划行事,赵国必亡,而他郭开,将成为秦国的功臣,享尽荣华!
想到这里,他嘴角扯出一抹阴毒的笑,低声喃喃:“李牧,就先拿你开刀!”
一月后,秦国咸阳,帝丞宫。
李斯手持密信疾步入殿,躬身呈予嬴政:“大王,郭开密信至。”
嬴政接过帛书,指尖掠过赵国君臣相残的消息,唇角不自觉扬起一抹玩味的弧度,这个郭开,倒真不负他所望,当初能逼廉颇出走魏国,如今又能劝得了赵偃杀了李牧,还真是将三寸不烂之舌使得淋漓尽致。
一月前放他归赵时,嬴政便与郭开密约,归赵后务必说动赵偃收李牧兵权,取其性命。
如今看来,这步棋下得恰到好处。
这些时日,郭开在赵偃耳边不断构陷,将李牧谋反的谣言说得活灵活现,勾结秦军,意图篡位,桩桩件件都戳中赵偃多疑的软肋。
更妙的是,赵国宗室对这位功高震主的将军早已忌惮多时,朝堂上下心照不宣的默契,终使赵偃下了杀心。
当解除兵权的诏书送达军营时,李牧却以社稷为重抗命不遵,可这铮铮铁骨,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。
嬴政摩挲着帛书,眼中寒光乍现,李牧这颗眼中钉,终究是拔除了。
而月前散布的“赵相劫持秦太后”之说,此刻正好师出有名,他抬眸望向殿外渐沉的天色,仿佛已看见大秦铁骑踏破邯郸的烽火。
又是一月后,赵国邯郸,龙台宫。
大殿之上,群臣面色凝重,一名斥候将军疾步入殿,单膝跪地:“大王,边境急报!秦军近日增兵十万,战车千乘,已逼近我赵国防线,似有进犯之意!”
赵王偃斜倚王座,闻言非但不惊,反而嗤笑一声,挥袖道:“嬴政小儿,当真以为我赵国无人?他要打,那便打!我赵国有精兵强将,何惧他秦军铁骑?”
群臣闻言,神色骤变,颜聚连忙上前,躬身劝道:“大王,不可啊!”
赵王眉头一皱:“有何不可?”
颜聚道:“大王明鉴,如今李牧新死,军中将士尚未归心,若仓促迎战,恐军心不稳。再者,秦国兵锋正盛,若我赵国独力相抗,即便能胜,也必元气大伤,反而让燕齐坐收渔利啊!”
赵王偃神色微动,但仍不甘心:“难道要我赵国向秦人低头?”
郭开见赵王动摇,立刻上前一步:“大王,臣有一计,可保赵国无忧,何不效仿当年渑池之盟,由大王亲赴咸阳,与秦王签订盟约?秦赵联手,共分天下,岂不比两败俱伤更好?”
赵王眯起眼睛,思索片刻,忽然大笑:“好!丞相果然深谋远虑!既然如此,那寡人便亲自走一趟咸阳,看看他嬴政敢不敢动我大赵!”
群臣面面相觑,有人欲再劝谏,却被赵王挥手打断:“不必多言!寡人自有分寸!”
殿内晨光映照出赵王自信而傲慢的面容,却无人察觉郭开嘴角那一闪而过的诡谲笑意。
十日后,赵王偃站在邯郸城的高台上,望着浩浩荡荡的出使队伍,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“大王,国书已送达秦国。”丞相郭开快步走来,低声禀报,“消息也已经散布出去,六国皆知您将亲赴咸阳。”
赵偃微微颔首,手指轻抚腰间玉佩:“很好,寡人倒要看看,这潭死水能被搅出多大的波澜。”
同一时刻,这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,在六国朝堂激起千层浪。
齐国,临淄。